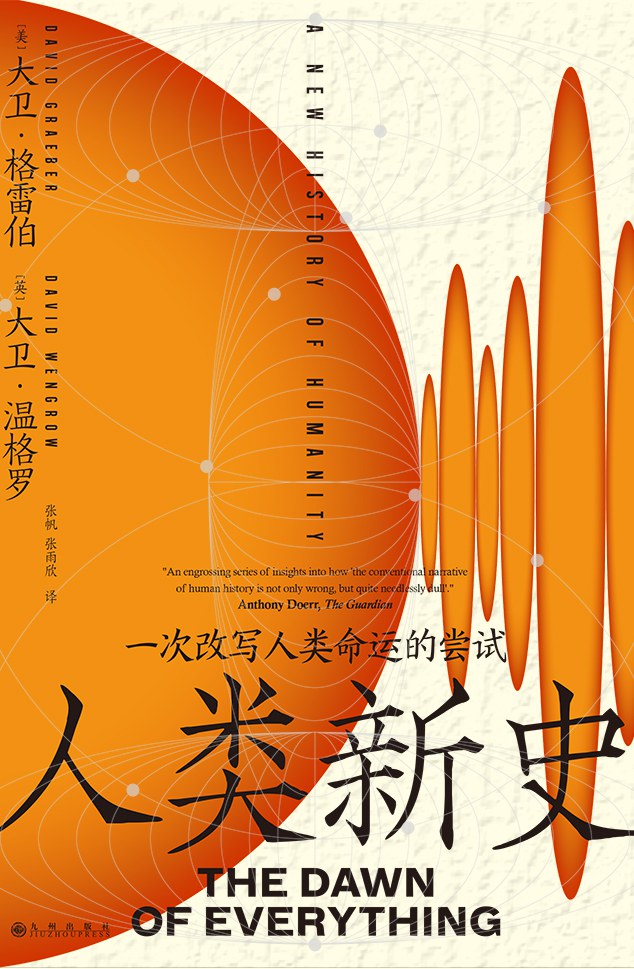对谈 | 许知远 x 大卫·温格罗:我们对平等的理解正确吗?(人类新史)书评-钻石棋牌
文选自经济观察报书评

人类学家的课题就是去理解人类所有的可能性,不只是与我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有着书店的城市社会——相似的那些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整个3万年人类历史中的所有可能性。
对谈 | 许知远 x 大卫·温格罗:我们对平等的理解正确吗?
《人类新史》是大卫·温格罗与大卫·格雷伯——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的一项历时10年的学术项目,最初“严肃的学术职责之余的消遣”,最终革新了人类大历史书写的范式。这是一部充满创新洞见的大胆之作,“二大卫”尝试摆脱概念桎梏,从更富于人性,也更贴近复杂历史现实的角度重新书写我们的祖先。

2024 年9月9日,本书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比较考古学教授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携新书《人类新史》与许知远以及本书译者张帆在单向空间·郎园店与朋友们分享了关于历史的另外一种叙事,也共同怀念另一位作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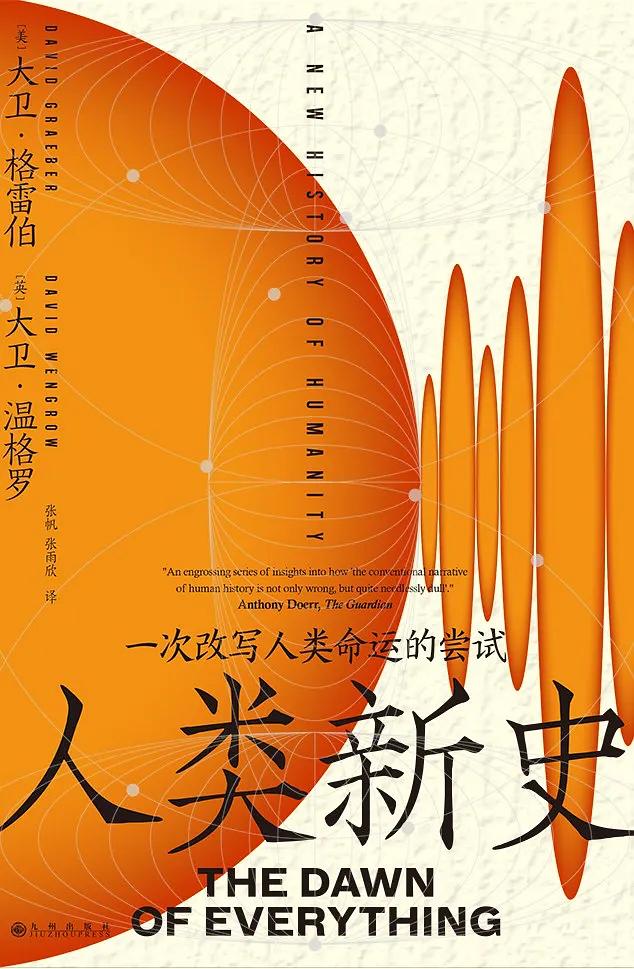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谈节选:
许知远: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实际上是对霍布斯和卢梭的两种人类历史模式的某种批判。你们最早是什么时候意识到霍布斯或者卢梭这两种模式的内在问题和困境的?这种想法是怎么慢慢浮现出来的?
多说两句,霍布斯的看法就是过去的人、原始人,是非常残酷、互相冲突的,必须有一个强力的国家才能带来基本的和平安定。卢梭的看法则认为原始人生活在非常平等自由的一种状态里面,只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大家失去了平等,越进入现代社会,越受困于新出现的国家,以及新的技术和发展,人们反而失去了过去的那种文明。他们俩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但这两种模式决定了我们很多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但这本书就挑战了这两种看法。
大卫·温格罗: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这本书,会发现我们并不是真的在批判霍布斯或卢梭本人,他们在自己的时代,也就是十七或十八世纪,显然是杰出的、堪称激进的思想家,人们直到今天还在谈论他们的洞见。我们真正的批判对象其实是那些当代作者。他们自称新霍布斯主义者或新卢梭主义者,把两位哲学家的理论,打造成了非常简化甚至博眼球的版本,那才是我们的批判对象。这些人的名字都在这本书里,可能许老师还访谈过其中的几位。
而且,我确定我们在书里说过——这本书很厚,但可以肯定我们在某个地方说过——卢梭其实是对的。他敏锐地捕捉到,我们这个物种确实失去了某样东西。只是他没弄明白失去的是什么。他猜测人类失去的是平等,而我们其实并不认为曾经存在过平等状态。但他问出了对的问题。

许知远:您跟大卫·格雷伯刚开始合作的时候——10年前吧那时候,你们最初对平等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大卫·温格罗:不止10年前,大概是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前后、十三四年前了。我们对平等的理解吗?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卫(格雷伯)那时已经写过相关主题的文章了,他认为如果没有等级,实际上也就无所谓平等。换句话说,逻辑上,只有参照一个地位更高的存在,才能谈论平等。比如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国王之下人人平等。
另一个让我们对平等概念感兴趣的点在于:为什么人们、尤其是社会科学家,总是假定小群体天然就是平等的,大群体天然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完全没有道理。就拿家庭来说,有谁听说过平等主义的家庭吗?我是说,大部分家庭究其本质都令人难以置信地不平等。未必就是父权制的,但小群体往往总会呈现出这样那样的极端不平等(译者补充:比如老人地位更高)。很难找到某种平等主义的家庭安排。可不知何故,我们头脑里就是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觉得平等主义在小群体中是自然而然的。就像格雷伯说的,大部分人其实根本受不了自己的家人,只想离他们远远的。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大卫专业领域内的文献,也就是人类学,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材料,他描述了一些社会,它们每年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节律性地改变自身的社会结构。群体的规模会改变,财富的分配会改变,就连整个社会的哲学和道德结构也会改变。就像把面具反复地戴上又摘下。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我们格外感兴趣的一个案例是北极靠南地区的因纽特人。大概100年之前,在更短的夏季,他们会散作很小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群体,到处捕鱼、狩猎。这样的小群体里等级极其分明,父亲就像个独裁者,欺压他的儿子们。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财产,执着于划分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
但在接下来更漫长的冬季,他们会重新聚合成更大的群体,一起住在用鲸鱼骨头搭建的壮观的冬季居所里。反倒这些规模更大的群体是平等主义的,人们共享一切,甚至会在海洋女神塞德娜的庆典上交换自己的伴侣。这跟我们通常设想的就完全不一样,小群体严苛并且等级化,而大群体其实还挺酷的。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很多人都对这样一种观点深信不疑,认为一个群体一旦突破了特定的规模,达到了特定的人口密度,就需要有人来领导,或是需要某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人们甚至用神经科学来佐证这种看法,比如根据“邓巴数字”的理论,人只能和150个人维系朋友关系,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就要创造某种管理结构。我想说,这在认知科学层面上没错,但就社会组织层面来说,基本就是胡扯。
所以我们想试试从更大的跨度上探究这个问题。让我们把考古学纳入考虑。我还记得大卫(格雷伯)有次问我,考古学里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一整座城市都是按照平等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的?
于是我开始向他介绍乌克兰发现的一些了不起的遗址。它们差不多有5000年的历史,跟中国或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市差不多古老。那些遗址中房屋的组织方式,看起来很像树桩的截面,排成一些巨大的圆环形。书里也有相关的图片。那里可能曾经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居民,就像其他那些古老的早期城市一样。
但科学家们拒绝把这些遗址称作城市。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没有庙宇,没有宫殿,没有官僚制,没有不平等的迹象。(译者补充:没有发现通常用来定义城市的一切标准。)这就有点荒谬了,实际上类似一种循环论证,城市必然有等级制,所以没有等级制的就不算城市。所以从定义上就不存在平等主义的城市。就算它有同样大的规模,有同样多的人口,也没有资格被叫做城市。
然后我们开始放眼世界其他地方。你常常会发现同样的情况,也许没那么极端,有些早期城市的的确确是等级制的,但另外一些其实并不是。就比如在巴基斯坦发现的,所谓的印度河文明,那里找不到任何一个国王或王后的形象,也没有王家墓葬。再看中美洲,古代墨西哥有不少精彩的例子,我们在书中有谈到,它们看上去相当民主,而同时期的欧洲社会还没什么民主的影子。
中墨西哥有个城市叫特拉斯卡拉,它是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最早接触的城市之一。当他开始入侵墨西哥的时候,他对当地人说,带我去见你们的国王——就像他在其他地方常做的那样。当地人说,我们没有国王。然后跟柯尔特斯说,你能不能先离开,几周之后再回来。因为我们要辩论一下这个事。
这场辩论,我们实际上找到了相关记录,非常好玩。内容类似:这都是些什么怪人呀?又脏又臭的,睡觉还不脱衣服,我们能相信他们吗?不过也许他们能帮我们呢?因为他们有奇怪的动物(也就是马),还有金属的剑,所以说不定能帮我们对付敌人,这样就能打败阿兹特克人了——他们已经和阿兹特克打了几代人的仗。最后他们决定加入西班牙征服者。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人能征服墨西哥,有两万多个特拉斯卡拉战士协助了他们。
今天当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谈到“枪炮、病菌与钢铁”,就像贾雷德·戴蒙德的那本书,可我们从来不会提到,事实上,造就这段历史的还有一个十六世纪的原住民城市议事会的协商。我甚至看到有些现代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会认为,那些原住民只是装出民主的样子,目的是要打动欧洲人,这种主张很没道理,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完全生活在君主制下面,怎么会被民主打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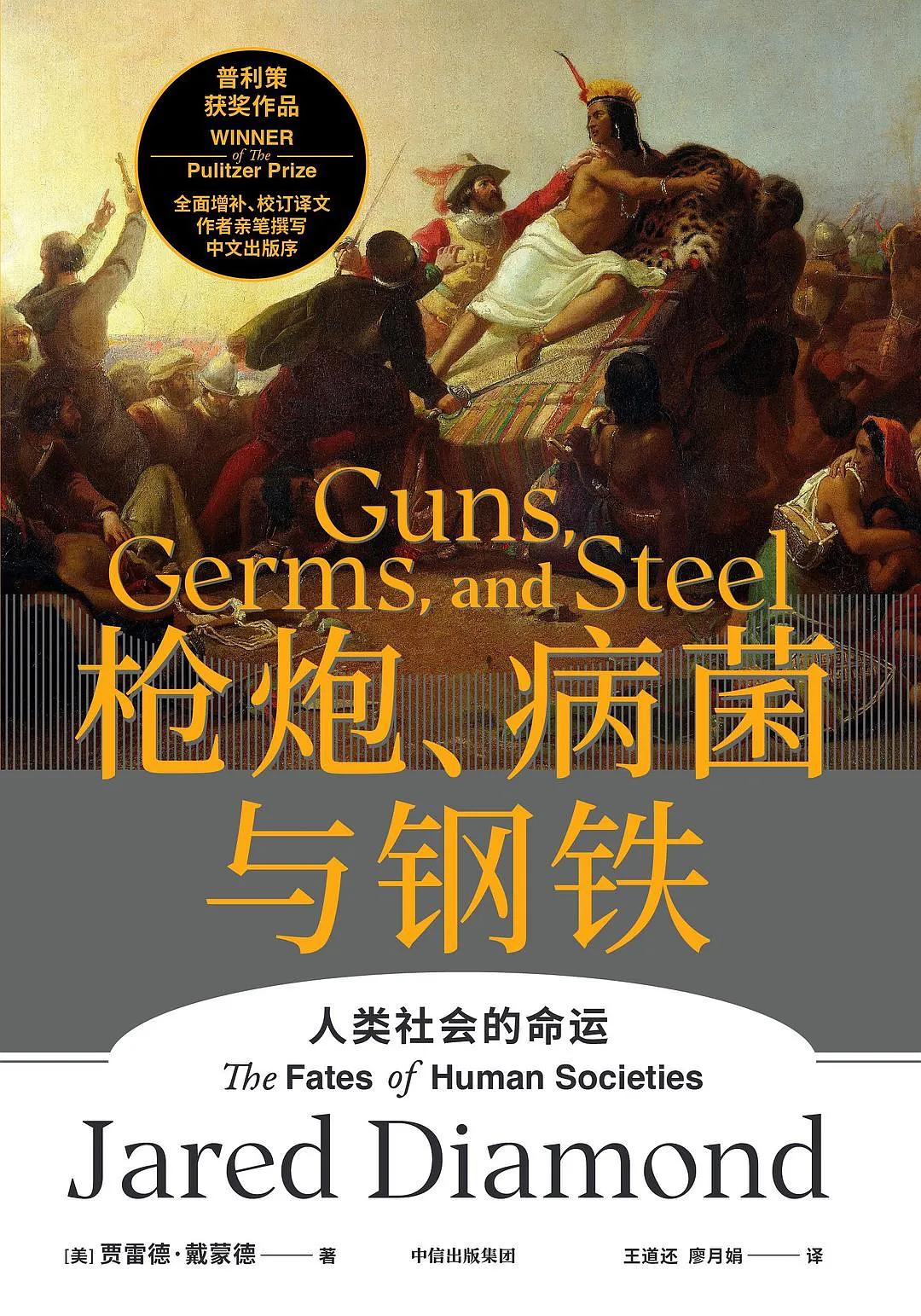
许知远:这本书等于是一个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您感觉一个考古学家的视野和一个人类学家的视野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然后互相的启发是什么?
大卫·温格罗:哦,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回答方式,但我的第一反应是,考古是一种非常社会性的活动。你在团队里开展工作,通常是一个大队伍一起去到考古现场。有点类似戏剧制作中的剧组工作,非常社会性。当然了,你的关注点都是过去的物质遗存。人类学研究可能是一段非常孤单的体验。你真的是一个人跑到异域的社会,作为当地的一个观察者,但并不真的属于那里。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处境。所以说人类学家倾向于单打独斗。
但归根结底,至少我个人认为,而我想大卫·格雷伯也会赞同的是,这两者实际上有着共同的课题,那就是去理解人类所有的可能性,不只是与我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有着书店的城市社会——相似的那些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整个3万年人类历史中的所有可能性。
许知远:每个思考者都有他的思想风格,您觉得你们两人各自的思想风格是什么呢?然后在一起碰撞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大卫·温格罗:我今天早些时候还在说,这很难形容,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类比就是:两个乐手在一起玩音乐。就像基思·理查兹和米克·贾格尔,出于某种原因,发生了些什么,然后就成了滚石乐队。但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情况是,碰撞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最后你们也就只能在本地的小酒吧演一演。所以我说不出为什么我和大卫能实现这样的沟通,这么轻松地在一起写作。我真的不知道。